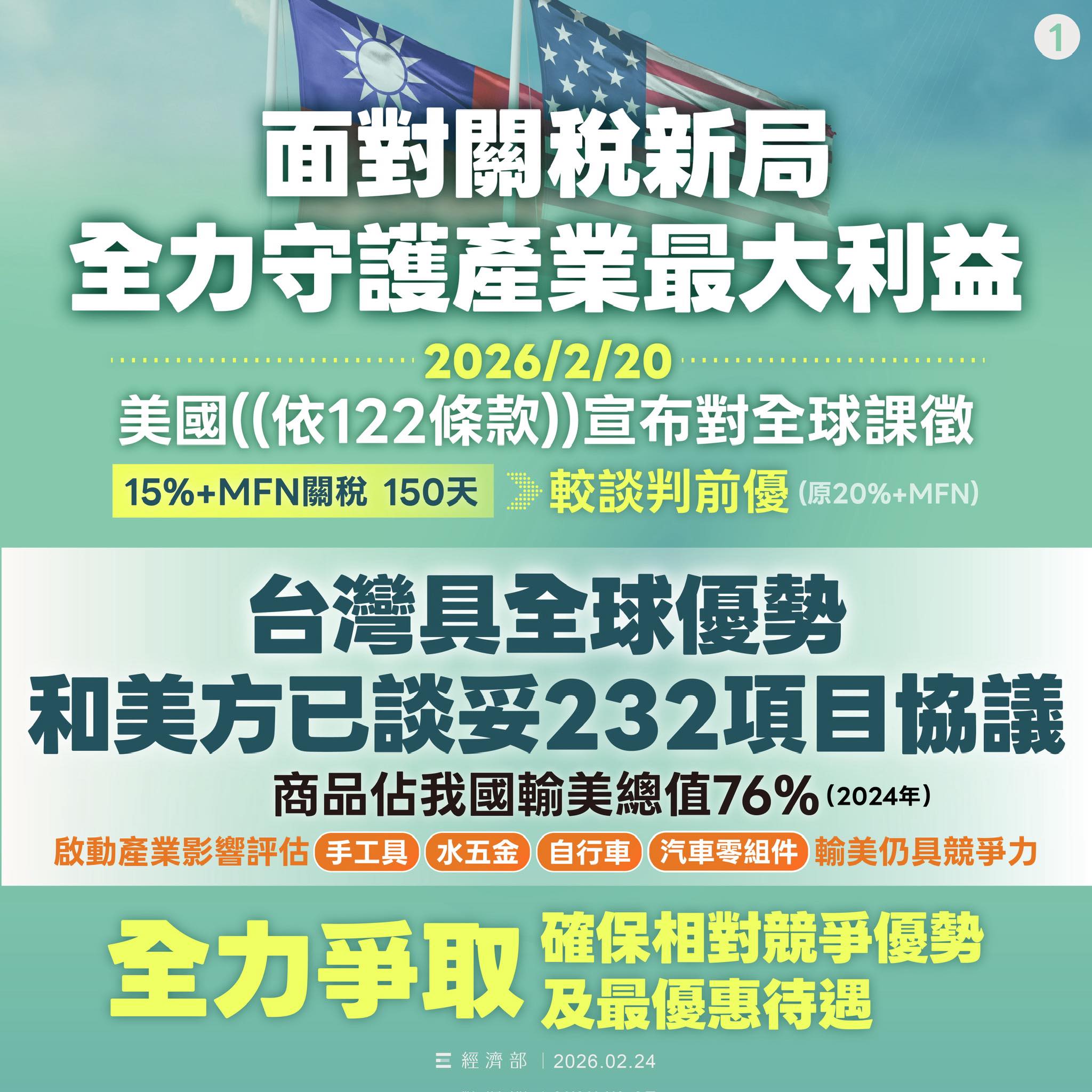:::

兩岸經貿關係新情勢及未來展望
隨著國際情勢及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改變,兩岸經貿關係也進入新階段。本文透過對兩岸投資、貿易的觀察,預測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新情勢,以及在陸臺商的未來發展。
脫鉤或鏈結?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
推力與拉力?影響大陸臺商的結構因素
影響臺商投資大陸可從「推力」和「拉力」兩部分來看。「推力」方面,最主要是歐美國家對中國大陸的「去風險化」戰略;其次是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變化,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。「拉力」部分,主要是大陸「擴內需」下的潛在市場誘因,以及中共所謂的「惠臺」政策。
一、 推力:「去風險化」使得臺商必須透過「中國+1」規避風險
兩岸經貿關係新情勢及未來展望
- 資料發布日期:113-11-19
- 最後更新日期:113-11-19

文/黃健群(工業總會大陸處處長)
隨著國際情勢及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改變,兩岸經貿關係也進入新階段。本文透過對兩岸投資、貿易的觀察,預測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新情勢,以及在陸臺商的未來發展。
脫鉤或鏈結?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
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,可從「投資」和「貿易」兩方面檢視。基本上,兩岸之間的貿易是由臺商投資大陸所帶動,大陸迄今仍是臺灣對外投資主要地區,但金額和比重都呈現逐年下降趨勢:2018年臺灣赴陸投資還有85億美元,2019年即腰斬為41.7億美元,2023年臺灣對大陸投資僅有30.4億美元,占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11.4%,和2010年的83.8%相較,顯然有極大落差。
截至2023年底,臺灣1,714家上市(櫃)公司中,有1,209家赴大陸投資(占整體70.54%;上市690家,上櫃519家),累計投資金額達2兆7,356億臺幣,較前一年增加324億。其中以電腦及週邊設備業、電子零組件業投資金額較大。然而,2023年度臺灣上市櫃公司於中國大陸合計投資收益獲利4,489億臺幣,整體較2022年度減少52億;惟與歷年相較,獲利金額為歷史第三高;且同(2023)年臺灣上市櫃公司在大陸的投資收益,共匯回臺灣1,502億元,創下史上新高,連兩年(2022、2023)匯回金額破千億臺幣。累計至2023年,臺灣上市櫃公司於大陸投資收益共匯回8,542億臺幣,占累積投資金額的31.23%,亦是史上新高;顯示臺商赴大陸投資後,近三分之一收益全部匯回臺灣母集團,重新資金分配。
雖然兩岸貿易依存度下降,但中國大陸仍是臺灣最主要貿易夥伴,以及最大貿易順差來源。2023年臺灣對中國大陸(含香港)貿易總額為2239.5億美元,占臺灣整體對外貿易的21.2%。其中,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(含香港)金額為1522.5億美元,占整體出口比重達35.2%(最高為2020年的43.9%,順差為1004.02億美元),臺灣對中國大陸(含香港)貿易順差達805.5億美元。
值得注意的是,2023年臺灣的順差高達805.6億美元,比2022年的513.33億美元成長56.94%,成長率創下歷史紀錄。其中對中國大陸的順差為 805.5億美元,卻是近4年新低,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比也從最高的43.9%下滑到35.2%。但若扣掉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,臺灣貿易呈現幾近逆差的情況。
總的來看,由於歐美對中國大陸「去風險化」戰略,以及中國大陸本身投資環境的改變等因素,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逐漸下降,兩岸貿易額依存度因而降低;兩岸經貿關係正呈現結構性的改變。
截至2023年底,臺灣1,714家上市(櫃)公司中,有1,209家赴大陸投資(占整體70.54%;上市690家,上櫃519家),累計投資金額達2兆7,356億臺幣,較前一年增加324億。其中以電腦及週邊設備業、電子零組件業投資金額較大。然而,2023年度臺灣上市櫃公司於中國大陸合計投資收益獲利4,489億臺幣,整體較2022年度減少52億;惟與歷年相較,獲利金額為歷史第三高;且同(2023)年臺灣上市櫃公司在大陸的投資收益,共匯回臺灣1,502億元,創下史上新高,連兩年(2022、2023)匯回金額破千億臺幣。累計至2023年,臺灣上市櫃公司於大陸投資收益共匯回8,542億臺幣,占累積投資金額的31.23%,亦是史上新高;顯示臺商赴大陸投資後,近三分之一收益全部匯回臺灣母集團,重新資金分配。
雖然兩岸貿易依存度下降,但中國大陸仍是臺灣最主要貿易夥伴,以及最大貿易順差來源。2023年臺灣對中國大陸(含香港)貿易總額為2239.5億美元,占臺灣整體對外貿易的21.2%。其中,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(含香港)金額為1522.5億美元,占整體出口比重達35.2%(最高為2020年的43.9%,順差為1004.02億美元),臺灣對中國大陸(含香港)貿易順差達805.5億美元。
值得注意的是,2023年臺灣的順差高達805.6億美元,比2022年的513.33億美元成長56.94%,成長率創下歷史紀錄。其中對中國大陸的順差為 805.5億美元,卻是近4年新低,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比也從最高的43.9%下滑到35.2%。但若扣掉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,臺灣貿易呈現幾近逆差的情況。
總的來看,由於歐美對中國大陸「去風險化」戰略,以及中國大陸本身投資環境的改變等因素,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逐漸下降,兩岸貿易額依存度因而降低;兩岸經貿關係正呈現結構性的改變。
推力與拉力?影響大陸臺商的結構因素
影響臺商投資大陸可從「推力」和「拉力」兩部分來看。「推力」方面,最主要是歐美國家對中國大陸的「去風險化」戰略;其次是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變化,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。「拉力」部分,主要是大陸「擴內需」下的潛在市場誘因,以及中共所謂的「惠臺」政策。
一、 推力:「去風險化」使得臺商必須透過「中國+1」規避風險
2023年5月七大工業國高峰會(G7)廣島峰會提出去風險(de-risk)而非脫鉤(decouple)方式因應中國大陸所謂經濟脅迫(economic coercion)後,「去風險化」已成為歐美對大陸的既定戰略。雖然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陣營認為:與中國大陸的脫鉤並不現實且不符合其利益,但勢必從三個方面推動「去風險化」:一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投資;二是加大關鍵技術的封鎖;三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。
雖然歐美國家的「去風險化」機制尚不明確、也不具體;但大陸當局認為,「去風險化」不但是更為精細的脫鉤,其本質更是充滿潛在敵意的「去中國化」。若G7徹底的推動「去風險化」,在「小院高牆」甚至「大院鐵幕」策略及避免經濟脅迫原則下,未來不僅是中高階、關鍵性產業,就連低附加價值的代工產業,都將撤離中國大陸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。換言之,基於強化經濟韌性(economic resilience)的「去風險化」,意味西方國家希望透過全球產業鏈的重組,建構更多元的製造基地;透過弱化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角色,降低其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。
基此,對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臺商來說,在歐美客戶要求下,勢必進行生產基地的重新布局;換言之,就是所謂的「中國+1」─在大陸以外設置其他的生產基地,以因應歐美基於「去風險化」下衍生的貿易保護主義。然而,「去風險化」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,對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跨國企業來說,雖可能經歷「再全球化」的陣痛,但也可能迎來新的契機;對缺乏資源的中小企業來說,若其技術或產品沒有不可替代性,面對所謂的平行供應鏈,則意味著更為嚴苛的挑戰。
除了「去風險化」戰略,大陸勞動成本的逐年提高、「綠色發展」下環保要求的提升,以及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;再加上大陸本土業者競爭加劇、大陸對臺商優惠待遇減少,由過去的「招商引資」轉為「挑商選資」;此外,雖仍堅持「發展」但同時強調「安全」下,加大對產業的監管力度,都讓臺商身處相較過去更為艱困的投資經營環境。以上的問題形成促使臺商轉移產線、甚或興起「不如歸去」,撤離大陸的主要推力。
二、 拉力:大陸「擴內需」及「惠臺」政策
一直以來,大陸經濟增長多依賴投資和出口,因此呈現投資率過高、消費率過低的結構失衡問題。基於國際需求的衰退,大陸認為不能再依賴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支點;因而,如何利用大陸超大規模市場優勢,釋放內需市場潛力,讓以「擴內需」為主的「內循環」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,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「戰略基點」。
大陸的「擴內需」,可分為兩個部分:一是拓展投資;二是促進消費。在拓展投資方面,主要是由政府帶頭,投資包括鐵路、公路、機場,以及水、能源、環境等傳統基礎建設,再加上農村與公衛等領域;目的是加速區域及城鄉的平衡發展。此外,強化包含5G、AI、大數據、工業互聯網等「新基建」的布建,以期帶動產業的升級轉型。在促進消費方面,主要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,讓大陸民眾願消費、能消費、敢消費。
對臺商來說,隨著經濟與產業的結構性轉型,中國大陸不再只是臺商的製造中心,更可能成為臺商重要的利潤中心。因此,包括RCEP、一帶一路等市場的整合,以及屬於「境內關外」的22個自貿試驗區,還有大陸基於「融合發展」對臺政策推出所謂的「惠臺」政策,對臺商來說,都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制度誘因。此外,相較於許多國家,中國大陸仍具有較完整的供應鏈,且基礎建設具優勢,人力素質也相對較高。也就是說,大陸內需市場潛力、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、一帶一路商機、供應鏈完整、良好的基礎建設,以及人口紅利或人才紅利,都形成對臺商的「拉力」。
結論:撤離或轉型?大陸臺商的策略選擇
全球供應鏈、產業鏈重組下的兩岸經貿關係,仍必須透過對臺商的投資動向來觀察;而這又會因為「企業規模」和「產業別」呈現不同的態勢。
從「企業規模」觀察:基本上大型臺灣企業,有足夠資源進行全球布局;因此,會採取「中國+1」方式,轉移部份產能到大陸以外的地區,以「在地銷售、在地生產」方式避險。但由於長期以來建立的完整供應鏈產業鏈,以及大陸「擴內需」政策等因素,並不會完全撤離大陸。值得注意的是,這些仍選擇留在大陸的臺商,很可能採取「就地轉型」,試圖打進大陸供應鏈;或透過製造業服務化、二轉三(製造業轉服務業)、二轉一(製造業轉農業)等方式,持續在大陸找尋商機。
但資源有限或沒有資源進行產線轉移的中小企業臺商,因為要選擇完全退場或撤出不容易,將可能採取「就地轉型」或「以拖待變」策略。
從「產業別」觀察:大陸臺商將被引導投入大陸國家政策或發展目標的產業,例如新一代資訊技術、生物技術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裝備、新能源汽車、綠色環保。換言之,專精特新、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綠色化的新興戰略性產業、生產性服務業,都將是大陸引導臺商重點投資的項目。因此,對具研發能力、擁有高新技術的臺商來說,其在中國大陸發展將獲得更多政府資源及市場機會;但對以從事外貿、傳產為主,或是低附加價值、技術門檻不高的臺商來說,將面臨升級轉型,甚或轉移離開的壓力。
此外,在由原本成本考量轉向內需市場考量下,將加速在陸臺商的在地化鏈結;且隨著大陸產業政策,大陸臺商將群聚在特定區域;例如東南沿海的大陸臺商,將可能轉移到中西部、各地自貿區(特別是福建、海南)。
基此,在進口替代政策下,大陸對於來自臺灣低附加價值、或足以自給或另有進口來源的產品,將減少進口;至於大陸所需的資通訊或關鍵產品,大陸將透過政策優惠及市場誘因,更積極吸引臺灣企業赴陸投資。且西方「去風險化」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,將間接減緩兩岸貿易依存度。與此同時,大陸「擴內需」下的市場誘因,將可能促使部分臺灣企業進一步在地化。
總的來看,全球產業鏈重組兩岸經貿關係的新情勢,取決於上述「拉力」和「推力」的競合和博弈。也就是說,在一推一拉之間,或有臺商選擇繼續深耕大陸市場;或有臺商選擇轉移至大陸以外地區。無論如何,兩岸的投資、貿易,將呈現有別過去的全新狀態。
雖然歐美國家的「去風險化」機制尚不明確、也不具體;但大陸當局認為,「去風險化」不但是更為精細的脫鉤,其本質更是充滿潛在敵意的「去中國化」。若G7徹底的推動「去風險化」,在「小院高牆」甚至「大院鐵幕」策略及避免經濟脅迫原則下,未來不僅是中高階、關鍵性產業,就連低附加價值的代工產業,都將撤離中國大陸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。換言之,基於強化經濟韌性(economic resilience)的「去風險化」,意味西方國家希望透過全球產業鏈的重組,建構更多元的製造基地;透過弱化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角色,降低其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。
基此,對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臺商來說,在歐美客戶要求下,勢必進行生產基地的重新布局;換言之,就是所謂的「中國+1」─在大陸以外設置其他的生產基地,以因應歐美基於「去風險化」下衍生的貿易保護主義。然而,「去風險化」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,對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跨國企業來說,雖可能經歷「再全球化」的陣痛,但也可能迎來新的契機;對缺乏資源的中小企業來說,若其技術或產品沒有不可替代性,面對所謂的平行供應鏈,則意味著更為嚴苛的挑戰。
除了「去風險化」戰略,大陸勞動成本的逐年提高、「綠色發展」下環保要求的提升,以及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;再加上大陸本土業者競爭加劇、大陸對臺商優惠待遇減少,由過去的「招商引資」轉為「挑商選資」;此外,雖仍堅持「發展」但同時強調「安全」下,加大對產業的監管力度,都讓臺商身處相較過去更為艱困的投資經營環境。以上的問題形成促使臺商轉移產線、甚或興起「不如歸去」,撤離大陸的主要推力。
二、 拉力:大陸「擴內需」及「惠臺」政策
一直以來,大陸經濟增長多依賴投資和出口,因此呈現投資率過高、消費率過低的結構失衡問題。基於國際需求的衰退,大陸認為不能再依賴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支點;因而,如何利用大陸超大規模市場優勢,釋放內需市場潛力,讓以「擴內需」為主的「內循環」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,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「戰略基點」。
大陸的「擴內需」,可分為兩個部分:一是拓展投資;二是促進消費。在拓展投資方面,主要是由政府帶頭,投資包括鐵路、公路、機場,以及水、能源、環境等傳統基礎建設,再加上農村與公衛等領域;目的是加速區域及城鄉的平衡發展。此外,強化包含5G、AI、大數據、工業互聯網等「新基建」的布建,以期帶動產業的升級轉型。在促進消費方面,主要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,讓大陸民眾願消費、能消費、敢消費。
對臺商來說,隨著經濟與產業的結構性轉型,中國大陸不再只是臺商的製造中心,更可能成為臺商重要的利潤中心。因此,包括RCEP、一帶一路等市場的整合,以及屬於「境內關外」的22個自貿試驗區,還有大陸基於「融合發展」對臺政策推出所謂的「惠臺」政策,對臺商來說,都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制度誘因。此外,相較於許多國家,中國大陸仍具有較完整的供應鏈,且基礎建設具優勢,人力素質也相對較高。也就是說,大陸內需市場潛力、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、一帶一路商機、供應鏈完整、良好的基礎建設,以及人口紅利或人才紅利,都形成對臺商的「拉力」。
結論:撤離或轉型?大陸臺商的策略選擇
全球供應鏈、產業鏈重組下的兩岸經貿關係,仍必須透過對臺商的投資動向來觀察;而這又會因為「企業規模」和「產業別」呈現不同的態勢。
從「企業規模」觀察:基本上大型臺灣企業,有足夠資源進行全球布局;因此,會採取「中國+1」方式,轉移部份產能到大陸以外的地區,以「在地銷售、在地生產」方式避險。但由於長期以來建立的完整供應鏈產業鏈,以及大陸「擴內需」政策等因素,並不會完全撤離大陸。值得注意的是,這些仍選擇留在大陸的臺商,很可能採取「就地轉型」,試圖打進大陸供應鏈;或透過製造業服務化、二轉三(製造業轉服務業)、二轉一(製造業轉農業)等方式,持續在大陸找尋商機。
但資源有限或沒有資源進行產線轉移的中小企業臺商,因為要選擇完全退場或撤出不容易,將可能採取「就地轉型」或「以拖待變」策略。
從「產業別」觀察:大陸臺商將被引導投入大陸國家政策或發展目標的產業,例如新一代資訊技術、生物技術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裝備、新能源汽車、綠色環保。換言之,專精特新、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綠色化的新興戰略性產業、生產性服務業,都將是大陸引導臺商重點投資的項目。因此,對具研發能力、擁有高新技術的臺商來說,其在中國大陸發展將獲得更多政府資源及市場機會;但對以從事外貿、傳產為主,或是低附加價值、技術門檻不高的臺商來說,將面臨升級轉型,甚或轉移離開的壓力。
此外,在由原本成本考量轉向內需市場考量下,將加速在陸臺商的在地化鏈結;且隨著大陸產業政策,大陸臺商將群聚在特定區域;例如東南沿海的大陸臺商,將可能轉移到中西部、各地自貿區(特別是福建、海南)。
基此,在進口替代政策下,大陸對於來自臺灣低附加價值、或足以自給或另有進口來源的產品,將減少進口;至於大陸所需的資通訊或關鍵產品,大陸將透過政策優惠及市場誘因,更積極吸引臺灣企業赴陸投資。且西方「去風險化」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,將間接減緩兩岸貿易依存度。與此同時,大陸「擴內需」下的市場誘因,將可能促使部分臺灣企業進一步在地化。
總的來看,全球產業鏈重組兩岸經貿關係的新情勢,取決於上述「拉力」和「推力」的競合和博弈。也就是說,在一推一拉之間,或有臺商選擇繼續深耕大陸市場;或有臺商選擇轉移至大陸以外地區。無論如何,兩岸的投資、貿易,將呈現有別過去的全新狀態。